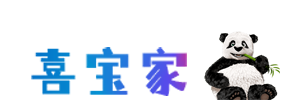升降散最早以僵蚕、大黄制方为雏形,治疗热疫之头面肿大兼喉痹,而后经过古代医家发挥、创新,增加姜黄、蝉蜕而终成方。此方用药精炼,制方严谨,功效立捷,善治热毒、火热怫郁于内或弥
升降散最早以僵蚕、大黄制方为雏形,治疗热疫之头面肿大兼喉痹,而后经过古代医家发挥、创新,增加姜黄、蝉蜕而终成方。此方用药精炼,制方严谨,功效立捷,善治热毒、火热怫郁于内或弥漫三焦的病证。文章深入分析升降散的理论渊源,为现代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价值。[摘要]通过对中医古籍中有关升降散论述的文献梳理,全面探讨其内涵。本方是在大黄、僵蚕为雏形的基础上增加蝉蜕、姜黄而成方,几经易名,终在杨璿《伤寒瘟疫条辨》中为后人所熟知。本方广泛用于治疗瘟疫,以丸剂、散剂为主,方便携带,便于服用;重用大黄旨在祛邪、逐秽;应用时视人之体质强弱和量其毒之轻重而判断用药多寡,并辅以米酒、生蜜等以顾护正气。杨璿将其由治疗“热疫”的专方扩展为治疗“表里三焦大热”的通用方剂,扩大了本方治疗疾病范围。升降散为温病名方,深受历代医家所赞誉和推崇,如清代医家陈良佐称赞此方“实卫生之仙剂,真捷效之神丹”;杨璿认为此方能“救大证、坏证、怪证、危证”;蒲辅周先生更是认为“温疫之升降散,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”。后人皆知升降散由大黄、僵蚕、蝉蜕、姜黄四味药物组成,但追溯其雏形只有大黄和僵蚕两味药。不仅如此,在各类着作中还存在方名不同而药物组成相同的现象,历代医家也有各自发挥。纵观现代文献数千条,观其临床疗效者十有**,探其理论发微者略见一二,却尚未有其古时应用之概貌阐述者。故详述之以加深对此方内涵的理解。

1 溯源
1.1 仅以大黄、僵蚕制方《儒门事亲》为金代医家张从正所着,成书于1228年,书中记载白僵蚕、大黄二药可治诸恶疮,又辑录“治大头病兼治喉痹(痹者,闭也)方:‘歌曰:人间治疫有仙方,一两僵蚕二大黄,姜汁为丸如弹大,井花调蜜便清凉。’”此歌诀指出僵蚕和大黄是治疗热毒壅遏上焦、发于头面而致头痛肿大如斗兼咽喉肿闭不通的主要药物。朱震亨《丹溪心法》也辑录此方歌治疗大头天行病。后至《御药院方》收集了金元及其以前的宫廷用方,书中记载用白僵蚕、生大黄治疗咽喉肿闭不通,名为五痹散。至明代,《普济方》中《咽喉门》记载如圣散(又名僵蚕散),治疗咽喉肿痛、痰壅喉痹,生姜汁送服白僵蚕末,重者含服大黄;《时气门》记载大黄僵蚕丸(原着无方名而后世编着者所命之方名)治大头病,兼治疫瘴。《古今医鉴》将僵黄丸列入《面病》篇而不是《瘟疫》篇,用于治疗胃中热盛上攻头面或风热外乘而致面肿,《东医宝鉴》中也收录此方治疗大头病及喉痹,并附歌诀。《中医方剂大辞典》中记载姜黄丸在《杏苑生春》中又名为二味消毒丸。古之方剂冠以“消毒”二字,皆有“消痈肿、解热毒”之用,此方似亦为热毒邪气所致病证而设。延至清代,《仙拈集》和《串雅内编》记载普济丹(僵蚕、生大黄、熟(制)大黄)治一切瘟疫时气、发热头痛及疟痢。
1.2 增加蝉蜕、姜黄以制方《万病回春》乃明代医家龚廷贤所着,书中记载内府仙方治肿项大头病、虾蟆瘟病,“僵蚕一两、姜黄二钱半、蝉退一钱半、大黄四两,上共为细末,姜汁打糊为丸”。龚廷贤为龚信之子,曾参与《古今医鉴》续编工作,应该很熟悉僵黄丸,又曾任太医院吏目,内府仙方本意为宫廷秘方,故龚廷贤或许是从太医院获取此方的。朝鲜医家许浚《东医宝鉴》中“僵黄丸”条下又有“加味僵黄丸”,附“即内府仙方”,暗示此方是在僵黄丸基础上增加蝉蜕、姜黄而成。

蝉蜕
姜黄

至清代,瘟疫横行,此方更是被奉为治疫之神方、效方。如《秘方集验》《经验丹方汇编》《文堂集验方》《寿世编》中列治蛤蟆瘟(大头瘟)方剂,虽无具体方名,但用药与内府仙方无异。陈良佐《温病大成·二分析义》用此方治疗热疫,以陪赈散命名,“窃谓岁饥有赈,犹赈济之不可无此药以陪之,故曰陪赈散”。后流传至杨璿,《伤寒瘟疫条辨》(以下简称为《寒瘟条辨》)如是记载:“是方不知始自何氏,《二分析义》改分两变服法,名为陪赈散……予更其名曰‘升降散’……又名‘太极丸’”。至此升降散作为温病名方而为后世所广为熟知。杨璿将陪赈散易名为升降散,其理由如下:其一,针对本方用药特点和功效而言,“盖取僵蚕、蝉蜕,升阳中之清阳;姜黄、大黄,降阴中之浊阴,一升一降,内外通和,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”;其二,仿刘河间“表里双解”之意,认为其作用与双解散不相上下,“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耳。名曰升降,亦双解之别名也”。但在《温证羊毛论》一书中,虽未提到升降散,却用其治疗羊毛温证,并易名为温证解毒散,方后又注明“或蜜、酒为丸,名太极丸”,且观书中加味凉膈散、加减双解散等组方用药,似与杨璿相差无几,仅是方名略有出入。从成书年代来看,《温证羊毛论》仅比《寒瘟条辨》晚10余年,或效法于杨璿已不得而知。而后《医方简义》《疑难急症简方》等书中均有升降散记载,但多为引用,鲜有发挥。
2 探析
2.1 理论渊源和发挥后人皆知升降散是杨璿辑录《二分析义》陪赈散、改两变服法易名而成,又盛赞杨璿在此基础上创治温十五方而为后世所用。殊不知治温十五方虽以升降散为其总方,而其中复苏、清凉、清化、神解等方剂均来源于《二分析义》。如《寒瘟条辨》辑录《二分析义》大、小复苏饮子均为原方原名,大、小清凉散由大、小清凉涤疫散变化而成。吕田汇集陈良佐、杨璿二家之言着有《瘟疫条辨摘要》,指出《二分析义》中载有代天靖疫饮子三方,《寒瘟条辨》仅录第一方,名为清化汤;有清心驱疫饮子三方,录第一方,名为神解散。陈良佐、杨璿治疫思想均来源于吴又可,但杨璿又有所发挥和创新。由此可见,陈、杨二家对升降散的推广应用均具有贡献,应相互参之。在陈良佐、杨璿二家论升降散的基础上,清代其他医家也有所发挥,提出自己的见解,列举如下以资参考。
刘奎对陪赈散颇有非议,在《松峰说疫》中以一例误治医案强调该方临床应用不可拘泥于“用治三十六般热疫”,以为与热毒相宜而放胆用之,此为误也;且人之病有在脏在腑之别,体质又有老少强弱之分,临床应用仍需细细辨证,斟酌得宜。罗汝兰对鼠疫病的治疗研究也体现了刘奎“不可一方治多病”的思想。罗汝兰称鼠疫虽同属瘟疫,但其病机为“热毒血瘀”,故不能混于他疫,若仅使用清化汤、升降散等清解之剂多不效,而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中活血解毒汤恰于此证合,用之犹宜。郑钦安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,他认为升降散与麻杏石甘汤同出一法,其理论依据为温病是温邪先犯太阳,又直趋阳明,伏于膈间,发为燥热,是二阳之正病,仲景立麻杏石甘汤实为以上证候具体治法,使邪气从太阳而入者仍从太阳而出。细品郑钦安之意,二方均有“透邪”的作用,既可治疗表里同病,又可治疗单纯里热证。但杨璿谓温病虽有表证状若伤寒,皆因里有郁火浮越于外,实为有表证而无表邪,升降散用轻清之品以升阳中之清阳,苦寒味厚之品以降阴中之浊阴,调理气机升降开导里热,里热除而表证自解;伤寒表里同病为外感寒邪,表寒未尽解又入里化热,麻杏石甘汤是辛凉药与辛温药并用,石膏凉能清泄,辛能发散,麻黄辛温开泄腠理引邪外出。由此可见,两方虽都有解表和(或)清里的作用,但用药和作用方式均不同,一为纵向一为横向。
2.2 临床应用探析
2.2.1 药解《寒瘟条辨》辑录《二分析义》中升降散方药之理而有所补充,甚是详尽。方中僵蚕其性轻浮而升,散逆浊结滞之痰,能治一切风热肿毒,辟一切怫郁之邪气,故为君;蝉蜕乃土木余气所化,属清虚之品,涤热而解毒,且取其蜕者退之意,使人病去而无恙也,故为臣;姜黄味苦性寒,下气最捷,破血立通,消瘴肿,故为佐;大黄气味俱厚,性大寒,阴中之阴,上下通行,走而不守,清脏腑蓄热,消痈肿,号称将军,故为使。大黄治疫以生用为多,而《仙拈集》《串雅内编》普济丹中却生、制大黄合而用之。探其缘由,大黄用酒浸制后,苦寒之性得以减缓,借酒之升散作用上达头部,以清解上焦热毒,应有增效之用。


生、制大黄自陈良佐之前,本方常用生姜汁为引,打糊为丸剂或调匀散剂。究其原因,或是因方中四药皆为寒凉之物,尤其大黄苦寒泻下,用量较大,易损伤脾胃,而配辛温的生姜以反佐之。陈良佐弃生姜易为米酒,米酒性热,味甘辛,甘则养气和血,辛则无处不到,用冷酒,能引诸凉药至热所,助药杀毒,尤为温病圣药。自古瘟疫治疗以攻邪为第一法门,陈良佐用米酒替代生姜,应是考虑到米酒兼有补养作用,防止邪去正伤。《寒瘟条辨》用黄酒冷服,实为米酒也,且断不可用蒸酒,因其蒸后仅存大热之性而辛散之力全无。蜂蜜为导,取其性凉、清热润燥而自散温毒也。如此六法具备,补泻兼行,寒热并用,治以热疫,其效甚速而其功甚神也。除上述引导药外,尚有记载用井花水和童便调药而服者。井花水是清晨首次汲取的井水,味甘无毒,“凉能清热,甘可助阴”;童便为十岁以下儿童小便,味咸性寒,走血分,有除邪热、清虚热作用,如《丹溪心法》中记载瘟疫热甚者可加童便。可见古时治疗瘟疫非常注重“热毒”和“阴伤”两大要素,取井花水或童便清热助阴之功效,便可两者兼顾之。
2.2.2 功效及应用升降散原为治疫所设,所治病证无外乎大头病、大头天行、大头瘟、虾蟆瘟、蛤蟆瘟、鸬鹚瘟,病名虽异,然皆为热疫也,症状相似。陈良佐认为热疫之源,系五脏之火发而移于六腑蓄积而成,升降散有升清降浊、散火除热功效,用之适宜;朱震亨认为瘟疫治有三法,宜补、宜散、宜降,且湿气在巅顶,不可用降药,升降散三法俱备,升降有序,亦为妙药。如果说陈良佐对升降散的应用还仅仅局限于治疗热疫,那么杨璿对此方的发挥可谓淋漓尽致。杨璿认为大头病等瘟疫皆因杂气由口鼻入三焦,怫郁内炽,治疗上非清则泻,非泻则清。升降散升清降浊,“升清可解表,降浊可清里,则阴阳和而内外俱彻矣”,故凡表里三焦大热,其证治不可名状者,皆可用此方治疗,但需随病之变化而随机应变,不可执方耳。杨璿对升降散誉不绝口,《寒瘟条辨》中多达30余处提到升降散,集中在卷二和卷三,或仅用此方,或合以他方,应用非常广泛。如合茵陈蒿汤治疗湿热郁蒸之面黄、身黄;合白虎汤治疗温病伏热内郁之咳嗽;合小承气汤治疗挟热下利。杨璿还提出升降散亦可用于产后温病,谓“如万不能不下,升降散无妨”;又创加味太极丸专治小儿温病。如此看来,《寒瘟条辨》堪称升降散应用大全,理、法、方、药析释全面,故蒲辅周先生大力推崇此书,认为治疗急性病、传染病,一定要潜心研读《寒瘟条辨》。

2.2.3 剂型变化古时医家多使用丸(丹)剂或散剂治疗瘟疫,源于瘟疫不同于普通四时温病,发病急,病情重,传变快,变证多,易发生广泛流行。而丸剂或散剂,有制药简单、服用方便的特点,省去煎药时间,尤其适用于治疗急性病、多发病、流行病,如陈良佐认为升降散并非贵重之品,按照比例增加剂量制成散剂以备不时之需。散剂又有容易吸收、药效迅速而猛烈的优势,符合瘟疫“驱邪务早、务尽”的治疗原则。此为其一也。其二,治疗喉痹,如《御药院方》五痹散及《古今医鉴》僵黄丸均可治疗咽喉肿闭不通,前者“用生姜汁、温蜜水调匀,细细服”,后者“井水入蜜少许,研,徐徐食后呷服”。之所以采取以上服药方式,除因咽喉肿闭不通致吞咽困难外,尚有使药物尽可能长时间停留在局部以便充分发挥药效的意义。其三,药名另有寓意,如杨璿“以太极本无极,用治杂气无声无臭之病也”之意取名“太极丸”,且变散为丸,可“缓下之”;陈良佐命之为散,又蕴含播散、扩散之意,即“散者散也,望仁人君子,量力施济,散给于人,传得寿世之也”。
2.2.4 剂量变化以大黄、僵蚕立方治疫者,大黄用量或倍于僵蚕,或与僵蚕等量,而以前者多见。后增加蝉蜕、姜黄而立方者,《万病回春》内府仙方用大黄四两、姜黄二钱半,但不同刻本中僵蚕、蝉蜕用量存在差异,如金陵周氏重刊本用僵蚕二两、蝉蜕两钱半,而扫叶山房木刻本中用僵蚕一两、蝉蜕一钱半。《中医方剂大辞典》记载内府仙方剂量与金陵周氏重刊本一致,僵蚕、蝉蜕、姜黄、大黄用药比例为2∶0.25∶0.25∶4;《寿世编》中四药比例为1∶0.12∶0.12∶0.2;陪赈散及升降散用药比例为2∶1∶0.3∶4。基本可以看出,除《寿世编》僵蚕用量大于大黄外,其余各方总体用药比例相似,均是大黄用量最多,僵蚕、蝉蜕次之,姜黄用量相对偏少。大黄自古被称为治疫之妙品,符合温病“逐秽为第一要义”的治疗**,故虽为佐药,却用量较大。

2.2.5 服药法及注意事项升降散无论是作散剂服还是作丸药服,均需用冷米酒和生蜜调匀。丸剂以大人每服一丸(每丸重一钱)、小儿减半为宜。至于散剂,陈良佐认为热疫发生时间为春分之后秋分之前,也正是因为春分至秋分占全年(365天)182天半而主张单次服散剂1.825钱。同时陈良佐也指出,若秋分后或春分前,即使有疫证也不能服此方,盖因此方因时制宜而专为热疫所设。但经杨璿对升降散阐释和发挥,可以看出只要恰合“热毒怫郁于内”或“火热弥漫三焦”的病机,便可灵活加减用之,不必拘泥于时间限制。此外,《串雅内编》《温证羊毛论》《寒瘟条辨》都提到服药需视患者之老幼强弱,量其毒之轻重,为服药多寡之准。针对服药注意事项,陈良佐提出宜空腹服,服药后忌茶水烟酒;宜清淡饮食及半饱,犹忌荤腥食物及过饱。此番考虑,乃因瘟疫治疗以“急急攻邪”为先,空腹服用有助于药物吸收而迅速发挥药效;又考虑药效猛烈、邪去中焦受损,不宜饱食或食用难以消化之物,总之以时时顾护正气为基本原则。
3 小结
综上,升降散最早可能以僵蚕、大黄制方为雏形,用以治疗热疫之头面肿大兼喉痹,而后经过古代医家发挥、创新,增加姜黄、蝉蜕而终成方。此方用药精炼,制方严谨,功效立捷,善治热毒、火热怫郁于内或弥漫三焦的病证。杨璿《寒瘟条辨》对其理法方药阐释最为详实、全面,可为不世之功,是后人广泛运用此方治疗外感及各种内伤杂病的理论来源和基础。现代应用升降散多变散剂为汤剂,剂量变化亦是各有所见,服药方法也因人因病而异,但仍需谨记“祛邪不伤正”的基本原则。
编者按:该文刊载于《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3期责任编辑:张怡
本文所用某些图片(或加工前原图)来自网络,若有疑似侵权行为,请确认后与我们联系,届时将予以删除。
作者:喜宝,采用[CC-BY-NC-SA]协议进行授权如无特别说明,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自:喜宝家
原文:基于中医古籍文献的升降散应用溯源及探析发布于:2023-06-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