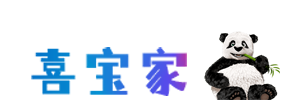神志异常,包括昏迷、谵妄、癫狂、不寐、善忘等,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病症。引起神志异常的原因很多,也很复杂,其中与血瘀的关系十分密切。临床应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治疗上述病症,常能获
血瘀证
神志异常,包括昏迷、谵妄、癫狂、不寐、善忘等,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病症。引起神志异常的原因很多,也很复杂,其中与血瘀的关系十分密切。临床应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治疗上述病症,常能获得满意的效果。本文试图从古今文献中,对血瘀而引起神志异常的主要证型和治法,略作探讨。
一、下焦蓄血
《伤寒论》载:“太阳病不解,热结膀胱,其人如狂,血自下,下者复。其外不解者,尚未可攻,当先解其外。
外解已,但少腹急结者,乃可攻之,宜桃核承气汤。”
又载:“太阳病,六七日,表证仍在,脉微而沉,反不结胸 ,其人发狂者,以热在下焦,少腹当腹满,小便自利者,下血乃复。
所以然者,以太阳随经,瘀热在里故也,抵挡汤主之。”
还说:“太阳病,身黄,脉沉结,少腹硬,小便不利者,为无血也;
小便自利,其人如狂者,血证谛也,抵挡汤主之。”
从这三条记述可以看出,太阳表邪随经入腑,瘀热互结膀胱的蓄血证,可出现发狂、如狂等神识反常的症候,
乃瘀热上扰于心,神明紊乱所致,诚如喻嘉言所说:
“蓄血至于发狂,则热势攻心……”仲景遵《内经》“血实宜决之”之旨,根据蓄血之久暂浅深,症情之轻重缓急,
分别以桃核承气汤、抵挡汤(或丸)活血祛瘀,通里攻下,促使瘀热下夺,使邪有去路,其病自复。
温病学**叶天士说:“夏月热久入血,最多蓄血一证,谵语神昏,看法以小便清长,大便必黑为是。”
可见蓄血证伤寒有之,温病亦有之,温病亦有之,有关蓄血引起的神志异常的治验,古今文献不乏记述。
如《本事方》载:“有人病伤寒七八日,脉微而沉,身黄,发狂,小腹胀满,脐下冷,小便利,予投以抵挡丸,下黑血数升,狂止,得汗解。”
此案与伤寒蓄血证甚合,故投剂立效。今人还扩充其治,对杂病之癫狂,若证属瘀血而致者,师仲景之法,亦多取效。
如李氏认为,现代医学所说的精神分裂症,类似中医躁狂症,多由七情致病。
在发病机理上,气郁不仅化火,也能使营血瘀滞,瘀血又使气郁加重而火炽,二者互为因果。
用活血祛瘀药,一方面减少因血瘀造成的气郁;另一方面瘀血得化,热无所附,则血行热散。
采用桃仁承气汤加减治疗精神分裂症30例,基本未复发。
叶橘泉老医师也曾介绍3例精神分裂症的治验,其中2例属蓄血发狂,均用桃核承气汤加减而后未复发。如:
患者施某,女18岁。初诊时被禁闭在小房内,蓬头垢面怒目炯炯,巩膜满布红丝。其势汹汹欲**,由其家属围护。
诊得脉沉细而弦,不肯张口伸舌,鼻下有血,唇色紫暗,腹部拒按,患者蹙眉示痛处,不食不眠,大便多日不下,
询之其母,已知两个多月不见经信来潮。
本例与下焦蓄血发狂相符,遂用桃仁承气汤与抵挡汤治之。
处方:
桃仁、鲜生地、芒硝各12克,生大黄、朱茯神各9克,桂枝、水蛭、虻虫、赤芍、丹皮各6克,甘草4.5克。
服2剂大便得下,夜寐稍安,狂势渐减复诊于硝黄之量减半,
去生地加红花、丹参以活血通经,连服3剂,月经来潮,患者如梦方醒,仅感疲倦无力,乃以逍遥散味调理数日而复。
近年有用桃核承气汤、抵挡汤加减治疗肝昏迷者,
如姜春华老医师指出,重症肝炎若诊为“下焦蓄血,漱水迷忘,小腹急痛,内外有热”,
可与桃核承气汤合犀角地黄汤治之。
他还认为陈自明《妇人良方》用桃仁承气汤
“治瘀血,少腹急痛,或谵语口干,水不咽,遍身黄色,小便自利,或血结胸中,手不敢近腹,或寒热昏迷,其人如狂”,
此证描述近似重症肝炎肝昏迷,提示血结瘀阻,扰乱心神,活血逐瘀为对证之治。
二、热入血室
《伤寒论》载:“妇人中风,发热恶寒,经水适来,得之七八日,热除而脉迟身凉,胸胁下满,如结胸状,谵语者,此为热入血室也。”
又说:“妇人伤寒,发热,经水适来,昼日明了。暮则谵语,如见鬼状者,此为热入血室。”
“热入血室”何以会出现谵语,如见鬼状等神识紊乱症候?
要回答这个问题,先得搞清血室是什么。所谓“血室”,诸家看法不尽一致,
有认为是指冲脉(成无己、方有执等),有认为是指肝脏(柯韵伯等),
也有认为是指**(张景岳、山田氏等)。
笔者以为第二种看法为是。
理由是:肝为藏血之脏,其经脉抵少腹,绕阴器,与冲、任、**都有密切联系;
又肝藏魂,调节人的神志活动。
肝有病变,自能影响正常的神志活动而出现神识反常的征象;
再从“热入血室”的其它症候如寒热如疟、胸胁下满等来看,也与肝的病理变化密切相关。
由是观之,妇人经期适遇外感,泻热乘机与血互结于肝,肝失藏魂之职;
瘀热又上扰于心,神明不宁,是导致谵语如见鬼状的病理症结所在。
所以仲景治“热入血室”尤有阐发,叶天士指出:“热陷血室之证,多有谵语如狂之象”,
治法注重清热凉血散瘀,认为“当从陶氏小柴胡汤去参、枣,加生地、桃仁、楂肉、丹皮、或犀角等。”
薛生白说:“湿热证经水适来,壮热口渴,谵语神昏,胸腹痛,或舌无苔,脉滑数,邪陷营分,宜大剂犀角、紫草、茜根、贯众、连翘、鲜菖蒲、银花路等味。”
亦体现了清热凉血散瘀之法;
吴鞠通谓:“热病经水适至,十数日不解,舌萎饮冷,心烦热,神气忽清忽乱,脉右长左沉,郁热在里加减桃仁承气汤主之。”
旨在逐瘀泻热。
方后注云:“得下黑血,下后神清渴减,止后服。”显然兼受《伤寒论》蓄血证的影响,故立法如斯。
路子贤在论治春温“热入血室”时提出:“宜用小柴胡去半夏,加归尾、桃仁、山楂、丹皮、赤芍、广郁金、鲜菖蒲,破瘀透邪也。”
诸家结合温病的特点,在清热凉血散瘀上着力,是“热入血室”的证治得到了很大发展。
现举周凤梧老师治验一则,以资启发:
济南刘某,女,32岁。病伤寒已五日矣。1945年1月11日邀余诊治。
六脉弦大而数,舌苔厚而燥,乍冷乍热,口渴而苦,大便秘结,夜烦难以入寐。
据其夫述及病因:系于五日前携小儿赴大明潮作溜冰之戏,突感寒气逼人,此时正值经至,阅一日经闭而白带下注,恶寒发热头痛,自服犀羚解毒丸数日不效,致病情发展至此,卧床不起。
根据上述脉弦、苔厚、便秘等症,颇似阳明腑实承气证,
但据《金匮要略》“妇人中风七八日,续来寒热,发作有时,经水适断,此为热入血室,治之无犯胃气及上二焦”之旨,
遂拟小柴胡汤加凉血活血润下之品:
北柴胡、生地、火麻仁各12克,黄芩、姜半夏、党参、丹参、瓜蒌仁各9克,生甘草3克,大枣3枚,生姜2片。
1剂寒热退而大便通,胃思纳谷,夜能入寐。
次日复诊脉和苔退,惟感低热口干,头目眩晕,心烦,小便短黄,乃余热未尽,热邪伤津,
又拟益阴清热疏利之剂:生地、花粉各12克,玄参、麦冬、青蒿、生山栀、淡竹叶各9克,生甘草3克。
两进旋复。
三、营热血瘀
温病邪入营血,热毒煎熬营阴,因而成瘀,瘀热交滞血分。
盖心主血属营,瘀热上扰心神,故可出现神昏谵语等症。
此时清热凉血、清新开窍。势所必用,然则瘀血与热为伍,徒清热而不祛瘀,则热有所附,瘀阻灵窍,其病难解,故须配合活血祛瘀之品,方能奏效。
试观治疗温病血分证的主方犀角地黄汤,即是凉血散血并用,组方颇具巧思。
俞根初化裁本方而成犀地清络饮,治邪入营血,瘀热互阻心窍而致的神昏谵妄等证,颇为合辙,
何秀山评述说:“热陷包络神昏,非痰迷心窍,即瘀阻心孔,必用轻清灵通之品,始能开窍而透络,
故以《千金》犀角地黄汤凉血通瘀为君,臣以带心连翘,透包络以清心,桃仁行心血而化瘀……此为清清透络,通瘀泄热之良方”。
又如治疗营分证的主方清营汤,方中丹参一药,功擅活血散瘀,寓清营泻热之中,以防血与热结,亦大有深意。
近年有用清瘟败毒饮合血府逐瘀汤治疗热病神昏,
也有介绍用下瘀血汤合犀角地黄汤治重症肝炎神志迟钝而获效者,
提示清热解毒,凉血祛瘀合用,对营热血瘀而致的神识紊乱,可望提高疗效。
四、瘀阻脑络
脑为元神之府,瘀血阻于脑络,可使神志发生异常的变化,多见于脑血管意外、颅脑外伤、颅内肿瘤等病证,活血化瘀对此类病症亦有一定疗效。
如徐氏报道治疗“脑外伤综合征”(脑外伤3个月后,仍有头痛、头昏、失眠等症状,但无神经系统器质性损伤体征,
可诊断为本病)84例,其中对窍络瘀阻型52例,
采用通窍活血汤加减(当归、红花、远志、白芷、藁本、川芎、赤芍、桃仁、陈皮、大枣为基本方),取得了显着疗效。
李氏介绍治疗1例“乙脑”后遗症神志失常,症见恐惧、烦躁、不语、寐差等,服通窍活血汤30余剂,恢复正常。
按通窍活血汤擅治上部血瘀,药力可达巅顶脑窍,故瘀阻脑络孔窍者,尤为适宜。
又癫狂病证,昔贤论治多重痰火,惟王清任独具慧眼,
明确提出“癫狂一症,……乃气血凝滞脑气,与脏腑不接,如同做梦一样。”
阐明了气滞血瘀为本病发病的关系,并创制癫狂梦醒汤活血通络理气化痰为治。
实践证明,本方对痰瘀互阻包络心窍的癫狂,确有疗效。
如中国中医研究院已故名医王文鼎对癫狂之实证,每多先投本方以行气化瘀,继则以十味温胆汤等方调治,常获效验。
沈氏临床体会到本方对精神分裂症属狂躁型初发者效果较好,
对外伤,特别是颅脑外伤所致的中枢神经功能紊乱的兴奋型,疗效确切。
五、血府瘀结
“血府”是指隔膜以上的部位,以心脏为主。盖心主神明,瘀阻心窍,最易引起神志失常的症候。
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,主治血府瘀结而致的瞀闷、急躁、不眠、夜晚多梦等症。后世踵其法,获效甚多。
如颜氏治疗1例顽固性失眠,居则彻夜不寐,病已十余年,服安眠药罔效。
参合患者面部瘀斑累累,两目红丝,脉涩,舌紫等症候,辨证为瘀滞窍络,遂用血府逐瘀汤,
服3剂渐能入睡,服至30剂,病乃未复发。笔者对冠心病、神经衰弱等病所出现的心悸心慌、失眠多梦、情绪急躁,
证属血府瘀结者,多用本方加减治之,效果亦较满意。
六、邪陷络闭
薛生白《湿热病篇》载:“湿热证七八日,口不渴,声不出,与饮食亦不却,默默不语,神识昏迷,
进辛香凉泄,芳香逐秽,俱不效,此邪入厥阴,主客混受,宜仿吴又可三甲散。
醉地鳖虫,醋炒鳖甲。土炒穿山甲、生僵蚕、柴胡、桃仁泥等味。”
薛氏自注云:“暑湿先伤阳分,然病久不解,必及于阴,阴阳两困,气钝血滞,而暑湿不得外泄,
遂深入厥阴,络脉凝瘀,……心主阻遏,灵气不通,所以神不清而昏迷默默也。破滞通瘀,斯络脉通而邪得解矣。”
吴氏三甲散(鳖甲、龟甲、穿山甲、蝉蜕、僵蚕。牡蛎、?虫、白芍、当归、甘草),功在入阴搜邪,活血通络。
薛氏师其意而用于邪陷络闭,灵机不通之神识异常,为热病神昏的救治,别开生面,很值得借鉴。
今人有用此法治疗“乙脑”后遗症神呆失语等,取得了一定疗效。
此外,妇女产后血晕神志异常,亦可由败血攻心所致,
诚如《血证论·产后》所说:“下血少而晕者,乃恶露上抢于心,心下满急,神昏口噤,绝不知人,法当破血”宜用失笑散,延胡索散等。
本文摘自:(励志斋医论选)
本文搜集古今中医经典文献,论述了神志异常的活血化瘀治疗之法,收获了知识的你,为传承中医动一动手指,转给更多需要它的中医人吧!
作者:喜宝,采用[CC-BY-NC-SA]协议进行授权如无特别说明,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自:喜宝家
原文:中医古籍中的秘密:论血瘀与神志异常的关系发布于:2023-06-07